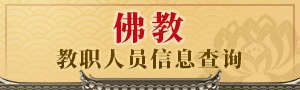杭州,永遠年輕
2019年6月,在海外醫(yī)藥公司有十多年神經(jīng)領域經(jīng)驗的吳博士辭掉了工作,從美國來到杭州醫(yī)藥港,開始了創(chuàng)業(yè)生涯。
他有一張漂亮的履歷,在大集團公司搞過科研,也在小初創(chuàng)公司帶過團隊,且不乏商業(yè)認知。放棄在海外多年的積累,回到國內(nèi)面對商業(yè)上的種種未知,既需要巨大的信心,也依賴足夠的勇氣。
從6月落地,到8月創(chuàng)立嘉因生物,吳博士僅接觸了五位投資人,10月,公司首輪融資就超過了1000萬美元。相比國外,國內(nèi)基因治療在研究上稍遜一籌,商業(yè)應用上更是幾乎空白。考慮到國內(nèi)基因治療領域藥物的高昂費用,一旦能夠?qū)崿F(xiàn)低成本應用,無論是商業(yè)價值還是社會價值都難以估量。
方興未艾的生物醫(yī)藥產(chǎn)業(yè),是過去幾年眾多在杭州扎根的新興產(chǎn)業(yè)之一。距離西湖30分鐘車程的杭州醫(yī)藥港,是杭州市發(fā)展生物醫(yī)藥產(chǎn)業(yè)的“核心區(qū)”,目前已經(jīng)聚集了近1600家生物醫(yī)藥企業(yè),全球十大藥企中有七家在這里落戶。
提及杭州,出場率最高的要么是以西湖為代表的湖光山色,要么是以電商為代表的互聯(lián)網(wǎng)黃金年代。但事實上,無論是制造業(yè)還是高新科技產(chǎn)業(yè),杭州的底子都不算弱。杭州的IC設計銷售規(guī)模常年穩(wěn)居全國前五,截至2021年7月,當?shù)?79家A股上市公司里,三分之二是制造業(yè)企業(yè)。
關于城市發(fā)展有過無數(shù)研究與學說,但有一個道理是相通的:一個城市的起落浮沉,總是與其產(chǎn)業(yè)的興衰緊緊綁定。
而如何吸引一個產(chǎn)業(yè),如何做大一個產(chǎn)業(yè),如何留下一個產(chǎn)業(yè),卻是城市治理中最復雜最深奧的難題之一。它的答案既隱藏在紅頭文件的字里行間,又閃爍在寫字樓里的一個個格子間,有時在車水馬龍的城際干道,有時又在城市郊野的無塵車間。
伴隨過去幾年生物醫(yī)藥、芯片設計、云計算等產(chǎn)業(yè)的紛紛崛起,杭州交上了一張優(yōu)秀的答卷。
01
產(chǎn)業(yè)的轉(zhuǎn)折
關于杭州,慣常人之中往往會有一個巨大錯覺:杭州沒有制造業(yè)。
事實上,早在1984年,杭州的工業(yè)產(chǎn)值就躋身全國前十,依靠的是以杭鋼、杭玻、杭重機等一批“杭字輩”大型工業(yè)企業(yè)。
改革開放初期,浙江是一片被政策忽略的土地,依靠自下而上的商品經(jīng)濟,浙江發(fā)展出了以鄉(xiāng)鎮(zhèn)企業(yè)為代表的小商品經(jīng)濟。比如嵊州的領帶、湖州的童裝、諸暨的襪子,隨便拎出來一個可能就是全球產(chǎn)值三分之一的占比。
但從產(chǎn)業(yè)視角看,小商品經(jīng)濟產(chǎn)業(yè)鏈短、附加值低,本質(zhì)上就是賺個人力成本的差價;“杭字輩”們雖然撐起了杭州的工業(yè)底子,但一是核心的設備和工藝依賴技術轉(zhuǎn)移,二是高能耗重污染,早晚得成為騰籠換鳥的對象。
所以,杭州并非沒有制造業(yè),而是制造業(yè)有規(guī)模,但缺少硬實力。
由于“杭字輩”的高能耗,杭州還出現(xiàn)過“保西湖還是保工業(yè)”的爭論。根源在于杭州主城區(qū)面積小,最終解決的辦法是把城市向外擴展,讓廠房建得離西湖遠一點。
體現(xiàn)在世紀之交的紅頭文件上,就是五大發(fā)展戰(zhàn)略中的“工業(yè)興市”和“環(huán)境立市”。
但搬離廠房并不能改變杭州工業(yè)彼時缺乏核心技術的問題,后來阿里巴巴依托杭州的成功,既是原杭州市委書記口中“廣種薄收的產(chǎn)物”[1],但互聯(lián)網(wǎng)產(chǎn)業(yè)的光芒也一定程度上容易讓人忽視杭州制造業(yè)大而不強的問題。
中美貿(mào)易摩擦給全國人民普及了產(chǎn)業(yè)升級的必要性,也讓杭州進一步審視了自己的產(chǎn)業(yè)結(jié)構(gòu),注意到了在先進制造方面的提升空間。在“專精特新”小巨人企業(yè)數(shù)量上(53家),前三批名單公布時,杭州在全國僅排第17位,是上海的五分之一。
抓住高附加值的新興產(chǎn)業(yè),帶動產(chǎn)業(yè)升級,成為杭州的核心目標之一。
但容易被忽略的一點是,產(chǎn)業(yè)升級對企業(yè)而言是一次長周期重投入的冒險,對地方政府而言,也意味著需要對舊有路徑依賴進行創(chuàng)新。
提及地方政府招商引資,經(jīng)典路徑是借助財稅、土地等政策傾斜,將產(chǎn)業(yè)龍頭的成熟產(chǎn)線復刻至當?shù)亍τ谄嚿a(chǎn)、電子加工這類領域來說,給政策、給補貼,把成熟產(chǎn)能平移到當?shù)兀瑢惡途蜆I(yè)的帶動立竿見影。但對高附加值的新興產(chǎn)業(yè)來說,卻很難適用。
最典型的是新能源車。新能源車固然是一張燙金的產(chǎn)業(yè)升級名片,但新品牌往往從創(chuàng)立到量產(chǎn)既需要漫長的成長周期,又依賴上下游供應鏈的配套,其間風險敞口不可謂不大。過去幾年,許多地方政府在新能源車上屢屢翻車,更是鬧出過被水氫汽車騙得團團轉(zhuǎn)的笑話。
究其原因,新興產(chǎn)業(yè)雖然附加值高,但大多需要動輒三五年的成長期,期間既要面對公司擴張中的治理問題,又要應付競爭對手和市場的不確定性。而對地方政府來說,拿著納稅人的錢押注新興產(chǎn)業(yè),既需要魄力,也需要耐心。
2021年3月,杭州創(chuàng)新基金啟動,年底累計完成組建規(guī)模444.44億元。今年上半年與紅杉中國的合作落地于城西科創(chuàng)大走廊,將選擇處于早期、成長期等不同階段的科創(chuàng)型企業(yè)作為投資重點。
這個創(chuàng)新基金是一個“基金集群”,由行業(yè)母基金、子基金和專項子基金構(gòu)成。母基金不僅可以投資項目,也可以投資基金;與紅杉的合作,屬于子基金;專項子基金主要聚焦戰(zhàn)略性新興產(chǎn)業(yè)和關鍵核心技術“卡脖子”環(huán)節(jié),針對杭州的重大產(chǎn)業(yè)項目,進行一對一的投資。
與紅杉中國的合作,標志著杭州創(chuàng)新基金離千億“小目標”更近了一步[6]。
歸根結(jié)底,對新興產(chǎn)業(yè)的扶持,不僅是對企業(yè)家的考驗,對肩負轉(zhuǎn)型升級重任的地方政府來說,也是一次既需要謹慎規(guī)劃,又依賴大膽下注的大考。
杭州的實踐已卓有成效:2021年,杭州工業(yè)經(jīng)濟實現(xiàn)2015年以來最高增速,規(guī)上工業(yè)增加值4100億元,同比增長10.6%[2]。近十年,高端制造業(yè)年均增長都達到了10%以上[3]。2022年,第四批“專精特新”小巨人名單公布,杭州155家企業(yè)入圍,創(chuàng)下新高。
事實證明,當輿論熱衷于討論杭州的房價和網(wǎng)紅的時候,杭州在集成電路、人工智能、生物醫(yī)藥等新興產(chǎn)業(yè)的押注,都陸陸續(xù)續(xù)步入了收獲期。
02
頂層設計
上世紀90年代,娃哈哈在杭州起步,宗慶后一度因產(chǎn)能緊俏焦慮不已,時任杭州市委辦公廳主任來到廠房考察,在目睹了熱火朝天的忙活和門外排隊等著運貨的卡車后,拍板支持只有130人的娃哈哈并購2000多人的國企罐頭食品廠。
這種企業(yè)家遇到問題,政府官員親力親為的圖景,是90年代水大魚大的典型場景,而這種景象如今依然在杭州復刻著。
坐落在錢塘區(qū)的奧泰生物,其中一項業(yè)務是抗原自檢試劑,是這個領域里不折不扣的隱形冠軍,90%的產(chǎn)品出口海外各地。然而疫情期間,藥監(jiān)局的第一批白名單里,卻沒有奧泰的名字。
當時,奧泰聯(lián)系了醫(yī)藥港,提出自己有為抗疫出力的意愿,也有相應的技術能力。醫(yī)藥港第一時間聯(lián)系到國家藥監(jiān)局,藥監(jiān)局則在第二周立馬來到現(xiàn)場核驗,通宵查看生產(chǎn)標準。沒多久,奧泰的抗原檢測試劑盒就進入了藥監(jiān)局的白名單。
在電商領域?qū)W⑵放迫阜盏奈米訒瑒?chuàng)立初期通過“出版”刊物的形式普及行業(yè)知識。不過,當時的書籍刊物都是免費贈送,因為公司不具備刊號。2017年,時任杭州發(fā)展研究會副會長造訪蚊子會后印象頗深,特意撰寫了一篇名為《“蚊子會”:一個公司的前世、今生和未來》的文章,把蚊子會形容成是“一個人的出版社”。
文章引起的反響熱烈,而當?shù)卣诹私馇闆r后,立馬著手幫蚊子會引薦了浙江人民出版社進行合作。從此之后,這個“一個人的出版社”也開啟了專業(yè)、規(guī)范的“三審三校”流程。
另一家脫胎于浙大光電學院的AI公司竺星科技,創(chuàng)辦于2019年。竺星科技團隊研發(fā)的“運動空間數(shù)字化”技術,以非接觸、免穿戴的形式,采集運動員在場上的數(shù)據(jù),既能對比賽進行分析,也可以生成個性化的球員卡。
浙大的校園為團隊創(chuàng)業(yè)初期提供了濃郁的創(chuàng)業(yè)氛圍,不僅有各式各樣的科技展會,還不斷有校友回來分享經(jīng)驗。走出校園,落戶余杭區(qū),竺星科技隨即感受到了來自政府的關懷。
對當時只有十多個人的團隊而言,余杭區(qū)600萬研發(fā)經(jīng)費的支持在當時資本的寒冬里可謂雪中送炭。竺星的故事,是未來科技城乃至杭州的一個縮影:當?shù)卣偸窃谕诰蚝蛶椭袧摿Φ钠髽I(yè)。
從這個角度來看,未來科技城提供了一個與校園“烏托邦”氛圍相當?shù)沫h(huán)境。用竺星創(chuàng)始團隊之一的黃文斌博士的話來說:“杭州就是比較敢試,無論是母校,還是政府,他們都愿意相信和培養(yǎng)我們這樣一個初創(chuàng)團隊。”
不過,“親臨一線的扶持”并不足以概括政府營造優(yōu)渥營商環(huán)境的全貌。事實上,高新產(chǎn)業(yè)集群趨勢明顯的當下,也對頂層設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有杭州市領導曾這樣表述政府和企業(yè)的關系:政府的核心戰(zhàn)略應該是環(huán)境立市戰(zhàn)略。換句話說,就是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務是打造一個一流的環(huán)境,因為只有一流的環(huán)境,才能吸引一流的人才,創(chuàng)辦一流的企業(yè)。而企業(yè)怎么辦,交給人才發(fā)揮就行。
這個觀點是對阿里巴巴成功的一種經(jīng)驗總結(jié),但對于如今成集群化的新興產(chǎn)業(yè)而言,也未嘗不貼切。
無論是生物醫(yī)藥、人工智能,還是大數(shù)據(jù)、芯片,這類產(chǎn)業(yè)有兩個非常鮮明的特點:一是人才密度極高,一家公司動輒一半人都有博士學位;二是產(chǎn)業(yè)鏈環(huán)節(jié)高度細分,以芯片為例,從上游的設備/材料,到中游的設計/制造/封測,再到下游AI、電子產(chǎn)品等應用場景,每一個環(huán)節(jié)都需要大量的人才規(guī)模和資本開支。
僅僅一個芯片產(chǎn)業(yè),既有上下游的緊密連接,又有每個環(huán)節(jié)大量的技術開發(fā)投入,需要的遠遠不是官員的一次力排眾議,而是一個關于營商環(huán)境打造的頂層設計。
對此,杭州給出的思路是“鏈長制”。通俗來說就是為一個產(chǎn)業(yè)匹配相應的產(chǎn)業(yè)鏈和政策,以及從源頭上負責的一位政府官員。官方出臺了《杭州市產(chǎn)業(yè)鏈鏈長制實施方案》,點明了智能物聯(lián)、生物醫(yī)藥、高端裝備、新材料和綠色能源五大生態(tài)圈。
而政府扮演的角色,一方面是產(chǎn)業(yè)層面的配套政策的頂層設計,另一方面是企業(yè)行政事務上的便利服務。企業(yè)發(fā)展的好不好,交由市場化的競爭去解決,政府既不是教練員,也不是裁判員,而是服務員。
在“卡脖子”重災區(qū)半導體產(chǎn)業(yè),坐落在西湖區(qū)云谷小鎮(zhèn)的平頭哥半導體公司,率先介入RISC-V架構(gòu),推動RISC-V架構(gòu)在國內(nèi)物聯(lián)網(wǎng)芯片取得領導地位,出貨量突破100億顆,與ARM和X86形成三足鼎立之勢。
今年8月,平頭哥發(fā)布首個高性能RISC-V芯片平臺“無劍600”及SoC原型“曳影1520”,首次兼容龍蜥Linux操作系統(tǒng)并成功運行LibreOffice,刷新全球RISC-V一系列紀錄。如果說RISC-V過去多用于中低端IoT市場,這次填補了高性能領域的空白。
在政府有意的布局下,杭州集成電路呈現(xiàn)出了“高新聚”的特征。“高”指的是產(chǎn)業(yè)高速增長:2021年,杭州集成電路產(chǎn)業(yè)實現(xiàn)主營業(yè)務收入413.5億元,同比增長25.7%,總量是2015年的2.5倍;“新”是創(chuàng)新活力迸發(fā):維爾科技、華瀾微等30多家企業(yè)參與了行業(yè)標準制定,300多家企業(yè)擁有授權(quán)專利;“聚”則是產(chǎn)業(yè)聚集的版圖清晰。
醫(yī)藥港也體現(xiàn)出了政府的這種集聚高新產(chǎn)業(yè),并提供專業(yè)配套和服務的思路。
疫情焦灼時,抗原試劑的需求一時大增,上游的一種膜狀輔料供不應求。這種輔料過去都是從德國進口,但當時價格一漲再漲,進口也多有不便。
企業(yè)在全省范圍內(nèi)搜尋輔料,終于在紹興找到了替代方。醫(yī)藥港的相關負責人直接和企業(yè)一起跑到紹興,希望對方能增加生產(chǎn)線,向奧泰生物供給所需輔料。在幾次合作后,這家公司甚至愿意直接搬到杭州來落戶安家。
放到城市和產(chǎn)業(yè)的語境里,這些案例各有各的可取之處,但在本質(zhì)上傳遞出的經(jīng)驗是一致的:高新產(chǎn)業(yè)的繁榮依賴的不再是英雄企業(yè)家的豪情一擲,而是無數(shù)研發(fā)一線的工程師一天一天累計的微小進步的厚積薄發(fā)。
因此,政府層面的規(guī)劃,既要有把控全局的思維和前瞻,又要懂得如何在細節(jié)上噓寒問暖。
03
永無止境的創(chuàng)新
奧泰生物的副總鄭孝君這樣評價在杭州創(chuàng)業(yè)的感受:“如果創(chuàng)業(yè)者在杭州呆的時間足夠長,我相信他不太會離開杭州”。
鄭孝君是技術出身,談論杭州的言語中少了幾分浪漫,但卻也可以從這樣直白的一錘定音中,聽出對杭州的偏愛。對很多初創(chuàng)公司而言,杭州的吸引力也是體現(xiàn)在方方面面的:
濃郁深厚的創(chuàng)新基因:這一點不僅體現(xiàn)不斷有創(chuàng)業(yè)者挑戰(zhàn)新產(chǎn)業(yè),同時也體現(xiàn)在政府營造的開明環(huán)境里。
開明包容的城市氛圍:用財經(jīng)作家吳曉波在《人間杭州》一書中的話來說,杭州是一個“沒有拒絕人格”的城市,愿意嘗試任何新鮮事物。于是,從電商到醫(yī)藥和半導體,新興產(chǎn)業(yè)不斷在杭州生根發(fā)芽。
能提供歸屬感的家園:無論是有一些資歷的80后,還是前來冒險的95后,都可以在杭州找到歸屬感。它可能來自產(chǎn)業(yè)園區(qū)里燈火通明的科研大樓,可能是帶貨聲此起彼伏的麗晶國際中心里的一戶loft,也可能是符合心意的餐館、景觀甚至夜店——在潮流的電音夜店,花5000元就可以把你的名字打在熒光屏上[5]。
1995年以前,杭州市區(qū)面積僅有430平方公里,戶籍人數(shù)130萬。在受限的空間里謀發(fā)展,可謂是螺螄殼里做道場[4]。經(jīng)歷了近30年持續(xù)的摸索和建設后,城市的面積是當時的40倍,常住人口達到了1200萬。
更重要的,是杭州對城市的建設和規(guī)劃帶來的啟示:兼顧因地制宜和多樣性,包容開放的同時,愿意為新銳產(chǎn)業(yè)提供扎根的土壤。
杭州醫(yī)藥港,從第一期建到了四期。很多時候,建設的轟鳴還沒有停下,有意向落地企業(yè)預定的訂單就已經(jīng)來了。未來科技城里,誕生了中國第一個“青年電商網(wǎng)紅村”。備受關注的半導體產(chǎn)業(yè),以平頭哥為代表的公司開始在芯片設計環(huán)節(jié)建立根據(jù)地。
因此,如果仔細觀察杭州的產(chǎn)業(yè)格局變遷,會發(fā)現(xiàn)無論是“杭州依賴互聯(lián)網(wǎng)”,還是“杭州沒有實體經(jīng)濟”,其實都是經(jīng)不起推敲的。事實是在眾多高附加值的新興產(chǎn)業(yè)中,杭州幾乎都有布局。
另一方面,將制造業(yè)和以軟件為代表的數(shù)字經(jīng)濟對立的思路,其實也是一種有失偏頗的產(chǎn)業(yè)分析視角。互聯(lián)網(wǎng)、大數(shù)據(jù)、人工智能這些朝氣蓬勃的技術手段,與制造業(yè)企業(yè)在供應、設計、生產(chǎn)、銷售和管理多環(huán)節(jié)的結(jié)合,推動制造業(yè)向高端轉(zhuǎn)型,早已成為共識。
浙江兆豐機電的生產(chǎn)車間里,傳統(tǒng)的有線和工業(yè)WIFI不見蹤影,取而代之的是無線5G網(wǎng)絡。生產(chǎn)車間采集的設備數(shù)據(jù)、AGV小車的運行數(shù)據(jù)等,都會通過5G網(wǎng)絡,匯聚到工業(yè)大腦平臺,深度挖掘數(shù)據(jù)價值。
杭州電信和兆豐機電共同打造的 “5G+ 柔性作業(yè)車間”,成功解決了傳統(tǒng)車間信號不穩(wěn)定的問題,將生產(chǎn)變得更靈活、更精準、更高效。
鏈長制方案,在明確產(chǎn)業(yè)方向的同時也劃定了目標:構(gòu)建智能物聯(lián)、生物醫(yī)藥、高端裝備、新材料和綠色能源五大產(chǎn)業(yè)生態(tài)圈,培育形成2個萬億級、1個5000億級、2個3000億級的產(chǎn)業(yè)集群等目標。
每當提起產(chǎn)業(yè)升級,似乎與之掛鉤的都是以芯片設計、半導體先進制程為代表的“高精尖”科技。但實際上,產(chǎn)業(yè)升級的內(nèi)涵,遠遠不止于此。
產(chǎn)業(yè)升級的真正含義,更多在于站穩(wěn)產(chǎn)業(yè)鏈上的高附加值環(huán)節(jié),繼而帶動整條產(chǎn)業(yè)鏈的創(chuàng)新方向。從這個角度看,許許多多的行業(yè)都有大量高附加值的戰(zhàn)略高地。
對于一座城市來說,她的產(chǎn)業(yè)升級就是想辦法吸引人才,想辦法留住人才,想辦法降低稅費、土地等要素成本,想辦法孕育高附加值產(chǎn)業(yè),繼而推動城市的繁榮。
杭州產(chǎn)業(yè)的故事,才剛剛開始。
04
尾聲
最近幾年,以“產(chǎn)業(yè)升級”為代表的一系列詞匯,在國內(nèi)外環(huán)境的快速變化下迅速普及。
和三十年前的“放權(quán)搞活”一樣,它看上去是個很好的詞語,是產(chǎn)業(yè)界振臂一呼的突圍路徑,是經(jīng)濟學家掛在嘴邊的靈丹妙藥,是政府官員日思夜想的遠大布局。
但具體到一個城市,它如何吸引新興產(chǎn)業(yè),如何做大產(chǎn)業(yè)集群,如何創(chuàng)造利稅與就業(yè),卻始終是一個復雜而深奧的命題。城市連同產(chǎn)業(yè)的繁榮,往往是風云際會的年代、銳意進取的企業(yè)、包容開放的政府組成的天作之合。
歸根結(jié)底,一座城市的朝氣,永遠來自年輕的產(chǎn)業(yè),和它背后一個又一個年輕的個體。
這是杭州的故事,也是中國的故事。(夏可欣)
版權(quán)聲明:凡注明“來源:中國西藏網(wǎng)”或“中國西藏網(wǎng)文”的所有作品,版權(quán)歸高原(北京)文化傳播有限公司。任何媒體轉(zhuǎn)載、摘編、引用,須注明來源中國西藏網(wǎng)和署著作者名,否則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。
- 假期臨近 多國呼吁民眾采取措施以防新冠傳播
- 央行:11月末,廣義貨幣余額264.7萬億元
- 平安健康上線新冠免費問診專區(qū) 單日訪問量激增137%
- 央行:11月份社會融資規(guī)模增量為1.99萬億元
- 北京120調(diào)度指揮系統(tǒng)緊急擴容應對呼入高峰 無危重情況請不要隨意撥打120
- 央行:11月末社會融資規(guī)模存量343.19萬億元 同比增長10%
- 《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中醫(yī)藥干預指引》發(fā)布 中成藥用藥一般不超過三至五天
- 亞定點醫(yī)院在多地啟用:已有多個縣改造本地醫(yī)院、衛(wèi)生院
- “陽過”何時可以返崗?一份“陽康”指南送給你
- 鐵證如山!這些文物講述南京大屠殺真相

 中國西藏網(wǎng)微博
中國西藏網(wǎng)微博 中國西藏網(wǎng)微信
中國西藏網(wǎng)微信